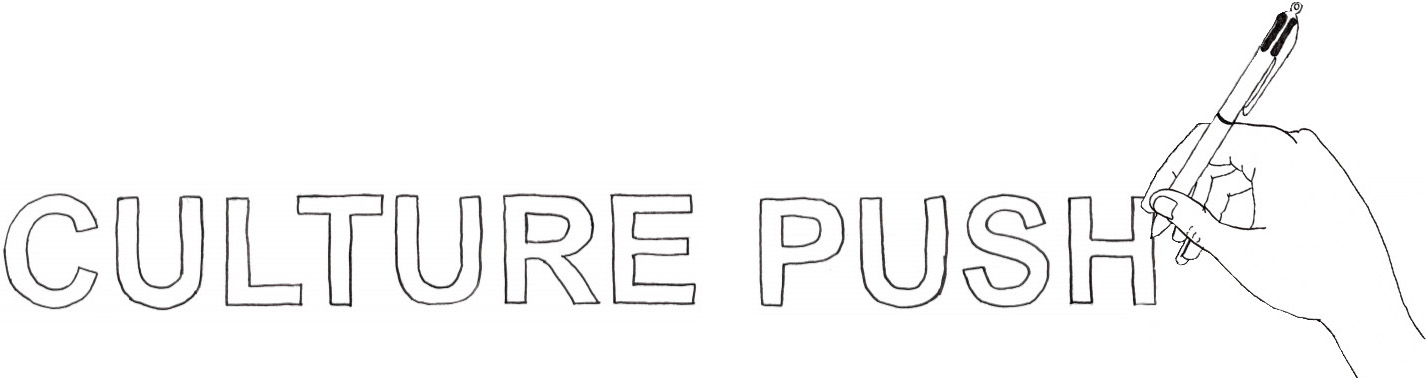还剑湖,河内,越南。摄影/陈慧莹
海外离散华人的真实:这一年,一个人的世界旅程
陈慧莹
这一年,我去了八个国家的唐人街,对离散与家园概念进行了跨国性的调查。作为卫斯理学院肯那佛(Knafel)计画学人,我自己独立规划了这趟四大洲的旅程-秘鲁、古巴、南非、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及中国,考察了每个国家独特的华人移民史以及最终成形的唐人街。选择这些国家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着渊远的移民历史-自19世纪初,即有成千上万的苦力搭船抵达该处-还有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我通常以唐人街为起点,再循线探索该国的历史及现今的移民社群。为了追寻家族在中国的根源,我见到了一群七十岁高龄才开始学中文的华裔古巴奶奶们,并记录了许多移民迁徙的故事、韧性及变化中的族群与认同。以下是五个主题、反省与心得收获。
1. 全球草根运动的影响
原住民土地权利运动,雪梨,澳州。摄影/Elaine Syron
我离开美国时,仍是巴拉克欧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我在哈瓦那住处的客厅目睹唐纳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我即持续探讨川普对海外社群的影响。去年八月,我第一次听闻三K党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集结,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在雪梨初次接触原住民黑权运动。澳洲奴役制度所奴役的对象是十九世纪时的原住民及太平洋岛民,而1960年代的原住民黑权运动从美国的民权及黑权运动中得到启发,以原住民自决为中心而构筑的运动,在数十年后终于取得一些胜利,例如成立了原住民法律咨询机构,原住民医疗机构以及社区教育中心,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仍持续组织并关注拘留中死亡、缙绅化、土地权利及结构性不义之补偿等议题。白澳政策,在20世纪通过一系列保持澳洲白人移民及英国化的法令,反映着美国于此之前的反移民政策,如1882年排华法案,时至今日,这两个政府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相同的政策,在马努斯岛拘留中心内的暴行,以及美国政府仍拒绝通过正式的梦想法案等,都是其中一例。这些相似性使我明白,西方帝国在通过系统性的压迫政策彼此会直接相互影响。然而,过去、此间、其后的抵抗与运动却也一样坚强。从原住民黑权运动、雪梨红坊区到纽约哈林区坚强的草根组织,不论主流媒体是否报导,人民对彼此之间产生抗拒及影响也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从澳州「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全国性原住民所领导的气候正义运动,运动能量正火力全开。
2. 变迁中的族群:华人作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
与海外华人社群共同生活时,我接触到劳工阶级移民在异国的各种故事,但也看见同一群人操着同样的种族歧视修辞。反省亚裔美国人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角色后,我更加理解就华人如何被归为有色人种这件事,其实是众说纷纭,且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华裔友人曾问我:「我们算是棕色人种吗?」,也有朋友写下了「没有所谓”华人”的正义」一文,即使我们看起来有所选择也是一样。
Chinatow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摄影/陈慧莹
旅行过程中,我见到华人确实可能因为身处的国家、历史脉络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当我比较了自己在古巴及南非的经验后,就看得更清楚了。哈瓦那的唐人街是一个主要为黑人的社区,混居着年长的古巴华人,包括非裔华人的后代,许多具有百年历史的华人协会组织也聚集在那儿。另一方面,约翰尼斯堡则有着长远的种族歧视及种族隔离历史,当地的南非华人主要是单一族群聚居,部分原因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使然,纵使在南非已历经数个世代的华人,仍生活在主要为华人的社区里。我拜访了两个约翰尼斯堡的唐人街,听到许多反黑人的情绪性言论,一些南非华人已内化地认为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有其必要。种族隔离的历史让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努力变「白」同时意味着追寻更高的自由。见到如此固着的种族主义想法以及两国间极端的差异,使我更加明白种族真真切切是一种社会建构。就像在美国的华人族群-特别是单一族群聚居者,会因为种族问题而集结起来,然而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模式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在美国「亚裔支持黑人活命」运动中,却看不见相同的动员能力。
3. 找寻家园
与秘鲁华人年轻人聚会,并分享纽约唐人街经验。利马,秘鲁 /摄影 Jorge Augusto Chang
在利马的前几天,辨认当地货币、公共交通以及了解单身女性如何安全地旅行等事让我极为忙乱,当我终于抵达唐人街时,挂在餐厅橱窗内的烤鸭、店铺口贩卖的糕点以及小时候熟悉的超市零嘴,唤起了家的感觉,让我再次记起为什么自己会选择来到这里。无独有偶,我在广州时,来自迦纳的友人也和我分享了相同的感受。当他第一次到广州时,他的朋友带他到小北,一个位于市中心、人称小非洲的地方。移民们多年来在此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邻里,并有着繁盛的商业活动,他的朋友也带他到可以安顿下来的社区。即使族群飞地正在经历全球性的变化,这些地方仍让许多人找到了家。
我与离散社群的人们越来越亲近,因为我们都有着追寻超越地理性概念「家园」的欲望。我与一群秘鲁华裔年轻人成为好友,他们充满好奇地彼此分享、交流对于在一个国家发展出家系世代一事的想法。对他们而言,同时身为华人及秘鲁人,需要一个意涵更广泛的词语,才能将混血族群身分认同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他们称自己为tusán,源自中文的「土生」(tǔ sheng),意思是在当地出生。聚会时,像是发现华人食物秘鲁化的过程,竟与其美国化的过程相同,还有土生认同运动的快速发展,都让我们共同感到惊叹。跟他们在一起分享故事、笑声,在中国餐馆咬下第一口食物时,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我提醒自己要相信这个过程,这些与他人心灵相通的时刻都是在因缘际会下触生。
4. 以酷儿、性别意识及非二元化的华裔美人姿态,生存及探索世界
还剑湖,河内,越南。摄影/陈慧莹
其实这并不容易。在家乡,纵使身处骚动混乱的美国,我都有一个彪悍的酷儿及跨性别亚裔美人社群能给我慰藉,他们是我的堡垒。然而在这一年当中我学到,为了生存与持续旅程,我必须在当地扎根,而非一直仰赖家乡的人们。这一年来,我并没有对大多数人公开自己的酷儿身分,几乎所有人都只认知我是个女人。有一段时间,异性恋与顺性别是全球挡也挡不住的性规范。在某些国家,因为我在种族及性别上被划归为单身、年轻的亚洲女性,街头骚扰甚至特别猖獗。顺性男会是第一个对我吹口哨的人,言谈间充满侵略性,或对我的研究主题夸夸其词地说教。进行家族寻根研究时,我最终找到一本与我家族同姓的族谱,但只有男系子孙的名字能被记载在上头。因为我不是男儿身,也不能传承家族姓氏,所以无法得到人们同等的尊重。虽然我身上流着强悍女性的血液,并且来自一个有色人种学生会教我如何悍卫自我主张的女子学院,但我仍有脆弱的时刻,我因为自己存在及成立的方式感到十分孤单。
然而,深入挖掘自身的力量,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社群。在秘鲁,我遇到一位酷儿,他教我西班牙语在殖民地发展出来的中性词汇,例如todxs 及amigxs (朋友),这也成为我们在whatsapp 上交谈的共同语言。在越南,我从脸书联系到河内酷儿(Hanoi Queer),一个常为酷儿社群举办聚会的团体,并参与了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我见到传统村里文化下的异性恋婚姻,使妇女牺牲自己只为了养育子女、操持家务,不禁使我深思,先祖辈的酷儿们是如何撑过来的。相信在殖民统治前,一定存在着几世纪之久的酷儿文化,即使无法浮出台面,但却彰显在今日人们的行动中。
5. 日常生活的韧性
母亲的故乡,泰山,中国。摄影/陈慧莹
摄影/陈慧莹
经过多年来在亚裔美人组织工作者社群的洗礼,我对何谓一个运动者有着清楚的理念与定义。然而,我在旅程中拓展了自己对行动主义的理解,发现其意义更加包罗万象。在古巴,有许多中国移民在1959年古巴革命后逃离,留下来的人不是因为相信新政府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离开。我遇到一些祖父母辈的长者,他们曾经历那段历史,而为了维持唐人街的存在,他们仍持续运作华人组织,纵使许多华人机构早已消失了。有些中文班的学生已经超过七十岁了,他们生平第一次学习中文,只为了与自己的传统有所连结。我回到我的祖父母们在中国的故乡,认识了那些曾与祖母一起在水稻田里耕作的老奶奶们。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女性仍留在当地,健康地活到高龄,从中国父权及贬低女性劳动力的体系里生存下来,她们从来没有用过「行动者」的字眼。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我遇到因生存迫切需求而组织起来的伙伴,他们没有任何资源协助。听他们分享华裔马来西亚人在唐人街如何保护社区并抵抗都市化迫迁,我震惊于他们的故事,与纽约、旧金山及波士顿唐人街反缙绅化的故事竟然如此相似。
回到纽约,日后,当我思考如何与在传统意义下政治语言及抗争想法都不同的人们一起参与运动时,我将记取这些日常行动的抵抗与韧性所教我的事。这趟旅程给了我希望,在不同的流亡时刻,华裔长者在公园里跳舞、下棋、玩牌,同时间也有著成千上万的集结正在发生。这样的想法已足够支持着我继续前行。